我是来自西安郊区的一名小镇青年,因为曾在夜店打工的经历,喜欢在工作之余去夜店拍照片。从九十年代到今天,我从西安,随着打工城市的迁徙,到广州、福州、杭州、乌鲁木齐,再到北京、上海,在每个不同的夜晚,记录了不同城市的夜店文化,也因此见证了夜店在中国的野蛮生长。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我把这些照片整理了出来,凑成了一段非正常生活的记忆碎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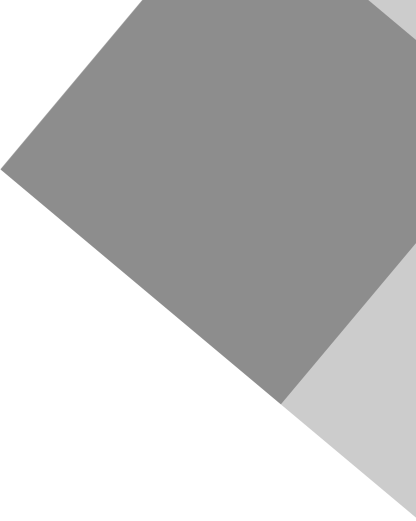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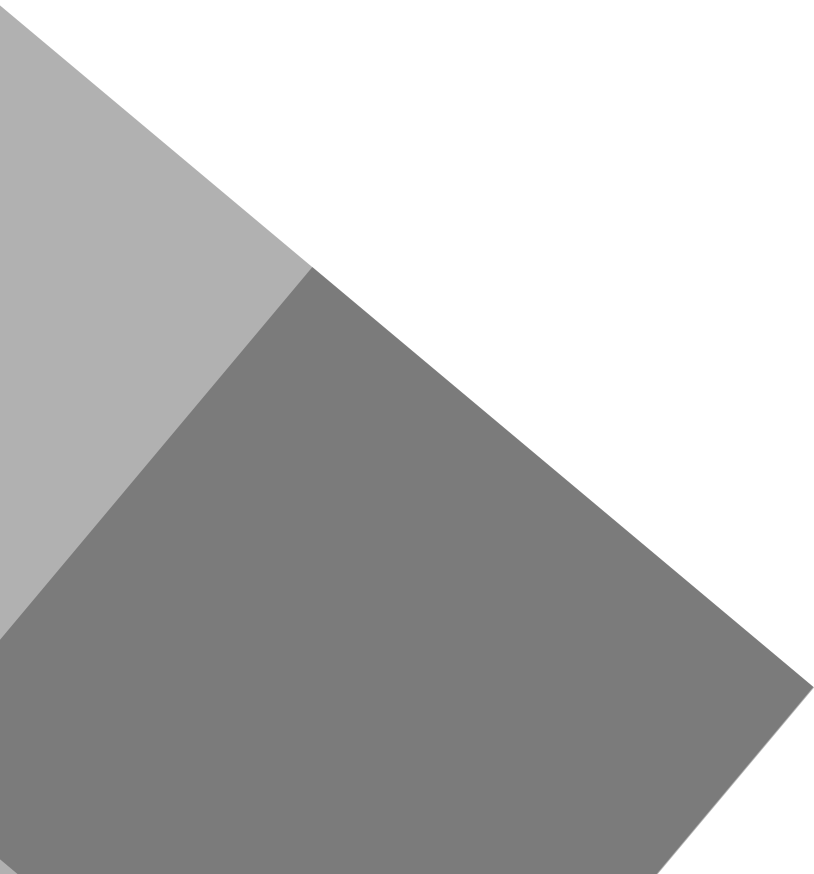















夜店生长
文/林爻大手
离那些地方远些
我的老家在西安108国道边的一个小县城,我对这条路的记忆除了吓人的车流,就是闪烁着霓虹灯的卡拉OK歌舞厅,这些招牌上常有的视觉信息是酒杯或是躺在酒杯里的裸女形象。
90年代初期是夜店这种舶来文化进入中国初具雏形的年代,霹雳舞、流行歌曲、卡带、单放机、太子裤、回力鞋,都是属于那个年代的记忆。那时候,十几岁少年正是喜欢模仿香港四大天王唱歌的年纪,我还是个接触新鲜事物较快、模仿能力较强的青少年,卡拉OK拿着话筒的神气劲儿对我们极具诱惑。
随着时间推移,居民们开始明白夜店这个晚上才开始营业的地方不是个正经地方,从里面走出来的男女也都不是些好人。大人们总是告诫孩子们,离那些地方远些再远些,谁要在那儿附近转悠就打断谁的腿。但越是这样告诫,越是惹得少年们好奇。
后来我进去过一次,才明白大人们警惕的地方原来是这么回事:外面水泥盖的房子,里面被软包成一些房间隔断,在一个50平米的空间里有几个来回旋转的彩灯,架着两个话筒,这便是当年的歌舞厅了,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跟电视剧《上海滩》里的夜总会也不一样。
DJ在一个有着玻璃面的房间里,手里拿着点歌单,对应着里面的编号,翻着一个黑皮的歌本,寻找对应的大LD黑胶唱片,并按排序放进LD放映机里。而当时流行的曲目大多是一些《革命歌曲》,《南泥湾》、《北京的金山上》,再流行一些的有《舞女泪》、《酒醉的探戈》、《把根留住》、《一剪梅》、《再回首》,最受欢迎的则是香港四大天王及陈慧娴的《千千阙歌》、《飘雪之类》的。
操着外地口音的女子
起风的三月,108国道上来了很多外地的女子,她们操着各种口音,打扮妖艳,穿戴极少。之后便常见一些中年男人骑125型日产摩托车,或开着黑色的桑塔纳轿车,又或是辆崭新的白色“富康”汽车而来。
一些大人聊天也会说起哪家舞厅门口,几个婆娘扒了一个“坐台的”衣服,“脸都抓烂了”是对那场打斗最有画面感的描述。那时候我还不能理解,唱个歌咋还要撕破脸。每次听到这样的传言,我都遗憾自己竟然错过,未能亲眼目睹。在那之后,故事越来越多,一家歌舞厅倒闭了另一家又开起来了,这些操着外地口音的女子也随之来了去了,一年又一年。
后来大众舞厅开始在出现在乡野的田间地头:用水泥抹出一片开阔地,挂几个彩色灯泡,支两个喇叭。舍得下本钱的主家会买个VCD机,再买个功放机和调音台、混音台,找个来回翻腾VCD放歌的大叔“野DJ”;不讲究的露天舞厅直接就放个双卡录音机,把音量开到最大,在门口横一把长凳子就行。来跳舞的大多是附近村庄的青年男女,收费1元还是两元则根据有没有VCD机和功放机来衡量。
那时候,乡村娱乐活动少,彩色电视也还未完全普及,供电也还分时段。晚上十点,乡村一片漆黑,除了田间地头的这些大众舞厅。在这方寸之地,也发生了不少的事情,大多是青年男性之间的争风吃醋,大打出手,或是在旁边的烤肉摊子上喝醉的双方争不下面子,而发生的动刀动枪事件。我已经不记得在那里发生的爱情最终有没有结果,但毋庸置疑的是每颗年轻的心都在那儿等待着被邀请。
而我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悄悄长大,旁观了那个时代的发展:BP机正在发挥着通讯作用,摩托罗拉翻盖手机已是做大事人的象征,诺基亚手机悄然入市……
在夜总会当服务生
我去西安上大学之前的暑假,在夜总会当过一个月服务生,月薪是300元,管吃管住。吃饭和那些外地来的小姐姐共在一个灶上,睡的是包厢的沙发。我的领班是一位带头大哥,偶尔给他跑腿买买烟,在他喝醉的时候拖他躺上沙发。
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唱歌,便在一位大哥的带领下去唱歌,唱的曲目是类似于《爱如潮水》、《谢谢你的爱》之类的流行歌曲,还在DISCO音乐响起时去跳霹雳舞,那时候特别盛行跳一些叫做太空、柔姿、滑步、弹簧步之类的,每当跳起时都会被围成一个大圈观看,而我就像一个耍猴的。
去大舞厅里玩的大多是一些时髦青年、社会小混混,经常会因为一些小摩擦或者某一个女生,打得头破血流。我当驻唱歌手没几天就因一场殴斗而终止了,但在那儿攒的人生经历可以说跌宕起伏,只可惜当时没有相机在手,纪录下来的影像会特别有趣。
小城青年的生活像贾樟柯电影里的小人物一样充满了躁动和不安,荷尔蒙催使下的炸裂青春无处安放。
门票五十元一张
1996年至1999年,西安,我多数时候是在旱冰场挥霍青春。在那个年代,我穿着牛劲裤、牛仔夹克、花格子衬衣,还有我的长发,随青春荡漾。我已经记不清那个旱冰场的名字,只记得陪我一起去的女同学。
那个旱冰场挺大,中间是一个DJ台,还有一个小舞池。我旱冰滑得不咋地,留恋的是那个小舞池。在那儿,我第一次听到了hiphop音乐,听到了rap,知道了“MC Hammer\迈克尔·杰克逊”,看到了几十号人在舞池中一起滑动舞步,那令我震撼不已。
除了旱冰场,就是刚刚兴起的DISCO酒吧。我现在还记得那家迪吧的名字叫“龙都”,但那不是我们能消费得起的高级场所,门票五十元一张,比一周的伙食费还要多。还好那时候校园里盛传着一些门票优惠券,原本是为了吸引女学生的,但被我们这些囊中羞涩的男同学拿来去学习新的舞步。
我也是在那时候暗地里发誓,将来一定要成为一名DJ,哪怕只是买一套打碟机摆在那儿。
几乎认全了西安的所有DJ
1999年,我离开校园进入社会,正式开始接触摄影。在一位恩师的指引下,决定开始拍摄个人项目,我为自己设立了两个目标:一个是夜店,另一个是摇滚乐,就这样一坚持就是十几年。直到现在,不管去哪座城市,必拍这两个项目。
正式开拍夜店项目前,我去几家夜店重新走访了一圈,最后锁定在西安古城玉祥门外的“焰吧”。在“焰吧”门口的小唱片店里,几个染着彩色头发,打扮前卫,走路轻浮的少年引起了我的注意。走进了解才知道,这家小店还肩负着为西北培养DJ的重任,而那几个奇装异服的年轻人都是在此接受培养的未来DJ。
决定拍摄的第一位DJ姓G,黄色的头色上点染墨绿色。我一眼看中了他的外型,后经了解,他还身兼多职,这更坚定了我选题的方向是对的。当年颇有经营头脑的他除了是DJ、夜场演艺经理,还自营着唱片店兼DJ培训班,又在一家音像器材公司担任高管。我佩服他旺盛的精力,不像有些夜场工作昼伏夜出的“夜猫子”,只晚上来劲。
跟拍他的那段时间,我努力记住了夜店音乐的分类,几乎认全了西安的所有DJ。在拍摄他们时,都会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拍这干啥?”大部分人对夜店都有着不好的印象,“性、暴力、违禁品”这样的词语总和他们联系在一起,夜店里充满了诱惑和陷阱,而没有人知道,这些服务于夜生活的人做的不过是一份工作而已,清者自清。
那组DJ的摄影报道后来刊发在当年的三秦都市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其他的一些纸质媒体上,DJ们觉得我为他们正了名,再以后去拍其他夜店就更加方便了。
小G带着那份报纸去了深圳,听说那是个很好的推荐材料,后来就失去了联系。前几年,通过微信朋友圈又不知怎么就联系上了,现在的他还依然活跃在夜场。跟他最近的一次聊天中,他向我反复强调:王哥,我现在已经不打碟了,搞管理……
在拍他的那个年代,用的还是胶片相机,我每次都会洗一叠送给他们,但估计只有我还保留着那些影像。十几年过去了,当年拍摄的那些DJ、Dancer们四散离去,有些人转行去当演员了,有的还继续混在夜场,不过也都当了管理人员,更多的则是和朋友们捆绑投资餐饮,听说好几位都成大款了,还有些彻底消失了。
只有去夜店最自在
2000年左右,数码相机开始在报纸发挥作用,胶片相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那时候,我所在的报纸经营困难,从日报改了周报,一大堆新闻记者下岗没了工作。
那时候,当年还叫photocome的一家图片销售公司和我签了图片版权合同,也就是现在的视觉中国VCG,《领舞女孩儿》的报道是我第一次尝试通过图片库的平台分发,最终这组报道得以在当年的新浪网上呈现。
看到这组图片时我已身在福州某快报做摄影记者,能在新浪网刊发这样的内容,让当地记者很是疑惑:“这能发吗?这是新闻吗?”我说,“适合传播并能引发关注的就是好内容。”
在福州停留的时间并不长,能从四季分明的废都到福州实在是受了杰克·凯鲁亚克的影响。《在路上》这本书实在“害人不浅”,但自从开始了我的自我流放之旅,夜店便成了我在陌生城市借以消愁之所。
很不幸,在福州夜店所拍摄的照片未能妥善保存。在迁徙杭州的旅途中,一个旅行背囊遗失,一段记忆从此被抹除。
2002年-2006年,我在杭州生活了将近四年,待了两家单位。从武林广场到断桥,从南山路的酒吧到夜店,从居住地楼下的“凡人咖啡馆”到黄龙体育场金碧辉煌的夜场,这几乎就是我的全部生活。
还好养成了走到哪儿拍到哪儿的习惯,夜店的故事也从此成为我在当地媒体刊发的第一组照片,这成了惯例。
2006年开春,我从杭州迁徙到乌鲁木齐。每去一个城市的当晚,我都会先去夜店,因为我觉得只有去夜店最自在,也最容易沟通。我向报社的同事打听最火的夜店竟没人知道,“谁去那地方!”
乌市夜生活比想象中丰富许多,我闻着味儿遁着声儿就摸进了一家酒吧,去得尚早,顾客并不多,正是搭腔说话的时候,看着DJ台后面的漂亮女孩儿戴着耳机在那儿操作唱机,我就知道来对了。两周之后,两组图片故事呈给了部门领导,一组《唱片骑师女DJ》和一组《领舞男郎》,洋洋洒洒几千字。
2006年五一假期后,我又从乌市迁徙至北京。来之后,决定让自己的生活节奏慢下来,不再去参与一线报道,安心做一个图片编辑。
我开始利用下班时间,报了个黑胶搓盘学习班,三个月之后学满毕业,出租屋的桌子上便有了一整套的威士达唱机和混音台。苦练了几个月搓盘技巧之后,我有机会去了一些很私密的派对打碟。音乐内容不像夜店那样以消费酒水为主要目的,而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那时候,我比较喜欢玩hiphop,毕竟有旱冰场的情结在,要不然就是迷幻电子,其他像Trance、Techno、House都太闹腾,一直不喜欢。有时间去夜店玩,我也绝不去工体那几家,五道口的一家小店生意不错,什么时候去都是座无虚席。老板给了我一张VIP,没排过队,心情好的时候便去拍几张。
寂寞与欲望交织的黑暗孤独
经历了2008年紧张忙碌后,2009年我暂别北京,带着整套的打碟设备,去上海和朋友开了家摄影公司,开启创业模式。可时间长了就又闲不住,几乎每个周末我都出现在上海大大小小的夜店之中,往来于各个派对。
对我来说,在夜店里拍照也从来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在夜店拍的时间久了,自然知道什么该拍,什么不该拍,什么时候该举起相机,什么时候该删除照片。老板除了安排给我一桌子的酒,有时候还安排几个黑衣安保人员负责我拍照的安全。一行有一行的规矩,一行有一行的门道。
我在上海积累了大量的拍摄素材,形成夜店系列图片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寂寞与欲望交织的黑暗孤独才是最终表达的主题。那时候,我从任何一个场子出来都不再觉得兴奋,反而觉得孤独。想去释放但却适得其反,这可能也是大多数想去买醉的人的真实感受。
2009年下半年,我再一次返回北京,在经过又一轮创业失败后,转行从事杂志与互联网、移动端的图片管理工作。慢慢地,我夜店去得越来越少,快门按得极其吝啬,有时候没按快门,就知道拍出来是什么样的画面,想想也就懒得再拍了。
在夜店里越来越觉得空虚,所以我逐渐远离了那个场所。现在的我有老婆孩子热炕头,回家倒头就睡着,根本来不及去想还去不去夜店。当年买的那套打碟机设备,摆放在新装修的房子里,也只是偶尔去摸几下,它存在的意义只剩下祭奠逐渐远去的青春。

欢迎联系我们
如果您有悄悄话想告诉我们,欢迎私信@看见微博;
如果您也有故事想通过摄影的方式来讲述,欢迎来稿。
邮箱:sinaphoto@vip.sina.com
《看见·看不见》新书已上市,讲述有力的图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