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的休渔期结束,宁波石浦港的渔船竞相出港。“东海潮涌,千帆竞发,渔民喜迎开渔……”当天,许多媒体以此为标题来形容开渔。但在许多专家看来,海岸线早已不堪重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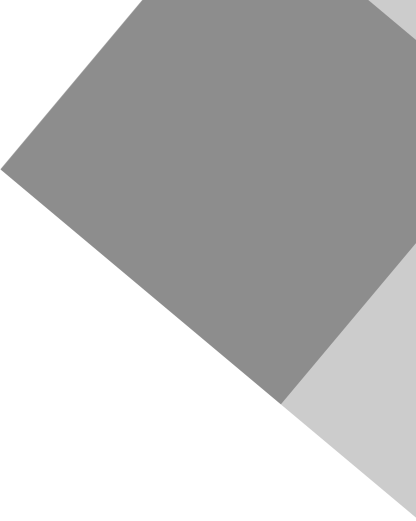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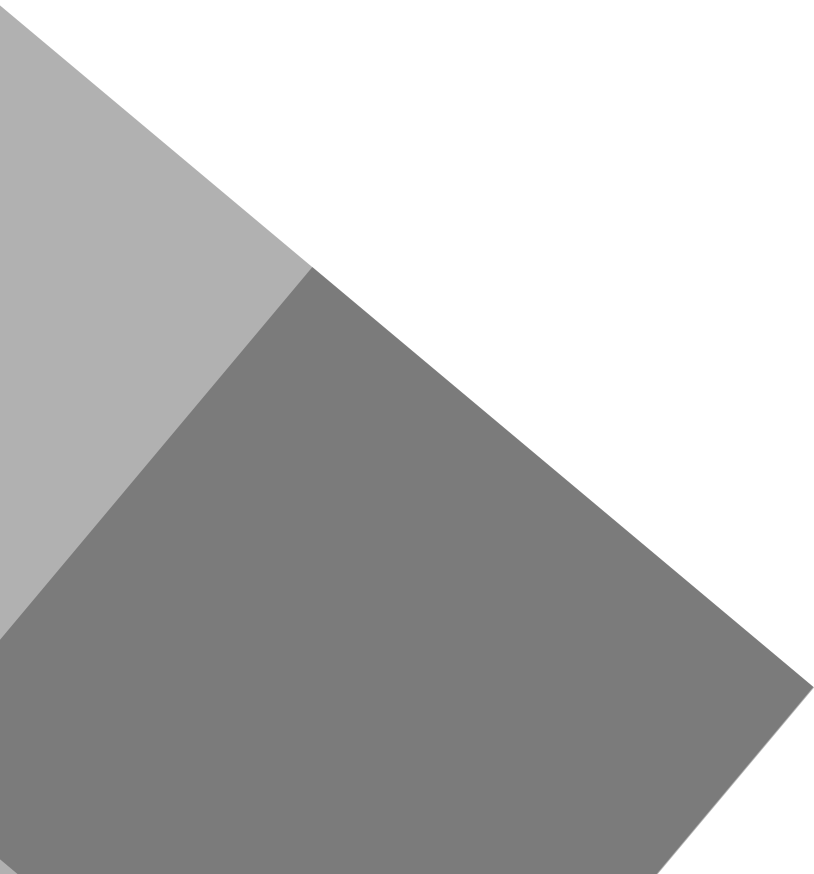
















中国东海系列(中篇)负重的海岸线
图/文 李颀拯
漳州市东山县宫前村的港口,黄友顺一边收拾渔具,一边接着电话,电话的那头,是相约来看船的买主。黄友顺,这个打了32年鱼的渔民,打算做完这一季,就把自己的小船卖了,去寻找其他的生计。具体做什么,他也没想好,眼前的这个海湾,已经很难让一家人的生活继续。赶小海,实在是没鱼了,一天的收入有时还不足百元。他想换个大船,可光船的造价就要上百万,最理想的也许是去远洋渔船上打工,因为村里很多人选择了这条路。
中国东海,沿着中国大陆的海岸线,它北起中国长江口北岸与黄海毗邻,南至广东省南澳岛同南海为界,濒临中国的沪、浙、闽、台4省市。面积77万多平方公里。这个曾经的世界四大渔场,如今已不得不面临东海无渔的尴尬。
海岸线是陆地与海洋的交界线,一般分为岛屿海岸线和大陆海岸线。在中国,海岸线总长度达3.2万公里。它是发展优良港口的先天条件。于是,往往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些沿海城市不竭余力地开发海岸线,将自然海岸线人工化,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围海造地。
当然,改变近海生态,让海岸线不堪重负的原因有很多,但很多人首先把矛头指向了掠夺式的过度捕捞;其次才是围海养殖、围海工业;还有通向大海的河流超标排放等问题。
千帆竞发,真的能喜迎收获吗?
2014年9月16日,浙江宁波石浦港,上千条渔船同时出港,“东海潮涌,千帆竞发,渔民喜迎开渔……”当天,无数媒体以此为标题来形容各地开渔节壮观景象,这样的大场面,当天不仅在宁波,还有舟山、台州、温州等地。半个月后,第一批出港的渔船回来了。船老大们没有如媒体所描述的那般“喜庆”,相反,他们个个愁容满面。“鱼太少了……” 少到什么地步?渔民罗胜概的捕捞日志中就有一串数字:10个小时,用直径70米、周长1000米的网,不停在海上横扫35海里,捕捞上的鱼只值一两千元。
这样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浙江海域。中国著名渔业专家、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仲霞铭说,舟山、宁波、温州……整个东海渔场都出现了相同的困境,东海已经到了无鱼可捕的边缘。
自1994年以来,中国的海洋渔业捕捞量一直蝉联世界首位。根据联合国粮农署最近发布的报告中显示的数据,2012年中国海洋捕捞量是位居全球之首,是第二名印度尼西亚的2.5倍多,约占全球捕捞总量的17.4%。
农民失地有补偿,渔民失海呢?
千百年来,农民靠山吃山,渔民靠海吃海。当有一天,农民失去了土地,还有土地补偿款。但当渔民曾经捕鱼的海被大面积压缩后,他们何来补偿?2000年后,中日、中韩、中越渔业协定生效,我国海上作业渔场被压缩;上海洋山港的建成,让国人为工业的发展大为赞叹,但它的背后是大片作业渔场被压缩;还有各种沿海的工业园区在不断扩张等等,这就是渔民在失海。
浙江海盐的东港村,位于海盐县东南沿海,东临乍浦港,南濒杭洲湾,沪杭公路贯穿全村,虽然老人们习惯于把门前的这条大河称做江,但在地图上,这里被标注为杭州湾。这是钱塘江的入海口,这里头顶的是跨海大桥,门前这条江里的水也是咸的,所以,被老人们称做江的这条大河,其实准确的定义,应该是海。
但这里的海,与我们在电影电视或者在旅行风光片中看到的海不一样,它就像一汪被搅混的泥汤水,一望无际。天空也总是灰蒙蒙的,站在海边,如果吹的是东北风,那你就会明显闻到一股刺鼻的工业原料味。那风是经过了东面不到一公里的化工工业园区后吹到这里。
东港村有965户人家。据村民方海平说,村里人原先一直以捕捞和养殖为业。最早时,他们与其他地方的渔民一样,每天开着船出去,撒网收网,然后拿着渔获去市场卖钱。但从2000年后,这里就发生了变化。65岁的老人郑福根说,他二十出头就一直做这行,等过了今年,他也打算把船卖掉不干了。“一来,可能是现在的水真是越来越脏,这些鱼都不愿意游到这儿来了,也有可能是前些年捕得太狠了,那时,每天上千条鳗苗是常有的事,现在每天的收获有时连支付油费都不够。你瞧,我们这些船上还有年轻人吗?他们都去了工厂了,只有老人还在做。”“二来,海边的房子也随着村里的土地被工业园征用了。本来还想为了拆迁的价格再去谈谈,现在每天闻着臭味,也实在受不了,想想还是快点搬走吧。为了多一点拆迁补偿,再待下去,命都少活几年的,算了,另谋出路吧。”
在福建沿海一线,这样的状况更甚。在漳州,大片的工业园区围海而建;大片的沙滩和海岸线上搭建着养殖场,一眼望去,可以延绵长达几十公里。数千条白色的PVC水管伸向大海,抽取着养殖用的海水,再将不经任何处理的废水直接排回大海,不少排放口还散发着一股腐臭味。已经从事中国海洋环保研究多年的专家周薇看到这场景直接说,“这样大规模的养殖对海洋生态的打击将会是毁灭性的,小规模分散性的养殖不但可以缓解人们对海产品的需求,也可以让野生物种休养生息。但这样的规模,可直接导致海水无法循环自净,最直接的反映就是赤潮频发。”本来渔民捕捞,可以放过的小鱼小虾,现在也有了需求的出路,他们可以加工成饲料,卖给养殖场。我们曾跟随一条小围网船出海,捞上来的全都是不到食指粗的小鱼苗。捕回岸上后,被饲料厂以一元一斤的价格买走。而船老大的收获也仅够柴油钱。
渔民远走他乡,发展海洋经济与保护海岸线生态互相冲突吗?
中国渔民更多地选择走向远洋捕鱼,是中国渔业发展的趋势使然,也是近海渔业资源枯竭背景下的无奈选择。中国沿海环境污染、围海造地,也迫使着中国渔民不得不改行。
岩头村,位于浙江台州老城区的东郊,曾经,这里被誉为东海之滨的鱼米之乡,这里的人们以收购交易渔获为生,如今发展成的医药化工“重镇”。岩头村,整村搬迁。
东港村,位于浙江嘉兴的杭州湾入海口,这里曾以捕捞鳗苗和蟹苗而红极一时,如今,也已开始搬迁,年轻人们大多去了旁边化工园区上班。
后头湾,位于浙江舟山的一个海岛上,由于交通不便、渔业资源枯竭,居民的谋生方式开始转变。近十年来,村民慢慢地都搬走了,如今整个村庄和港湾都空无一人。
后坑,位于福建云霄,村后的海湾已被大片养殖业占据,小渔船无处下网,只能换大船去往更远的海洋。
南屿,位于福建东山东南部,曾经门前沙滩的海湾里,每天都有30多条拉网作业的船只,如今,没鱼了,只剩下20多个老人和一条小木船。
古雷,位于福建漳州市漳浦县,曾经的大渔港,如今已是一片巨大的化工园区。
对于近海海岸线的过度开发而导致的严重后果,并非没有前车之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陷入发展空间狭小困境的日本,开始大规模填海造陆。在获得经济收益的同时,埋下了巨大隐患。自1945年到1978年,日本全国沿海滩涂减少了约390平方公里。很多靠近陆地的海域里,已经没有了生物活动,海水自净能力减弱,赤潮泛滥,日本渔业遭受重大损失。为此,日本曾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拆除人工海岸线,复原自然面貌。
对于正在加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中国,如何有效保护、利用海岸线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必须解决的课题。
编辑:秦翼 拍摄支持 | 绿色和平


























 依我看按照现在的捕捞方法,用不了10年渔民就没生存空间了。
依我看按照现在的捕捞方法,用不了10年渔民就没生存空间了。 [新浪网友]
[新浪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