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一场强沙尘暴经过,新建的古城隐没在黄沙中。中国共有262座资源型城市,有67座属于衰退型。它们中的一部分形成于建国之初,“矿市一体”模式占多数。这些城市曾经为中国经济建设倾其所有,如今却也步入“中年”,不得不面对随之而来的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经济衰退、贫困人口增多等压力。摄影师走访了8座资源型城市,用影像记录下他们的转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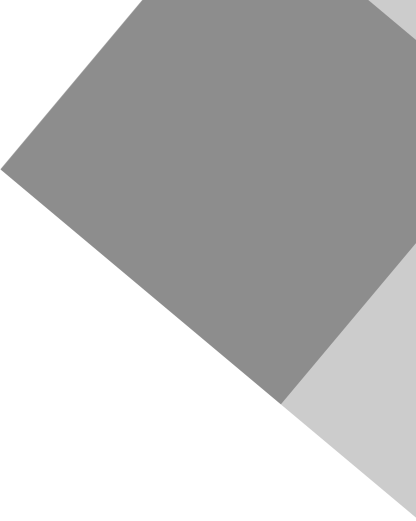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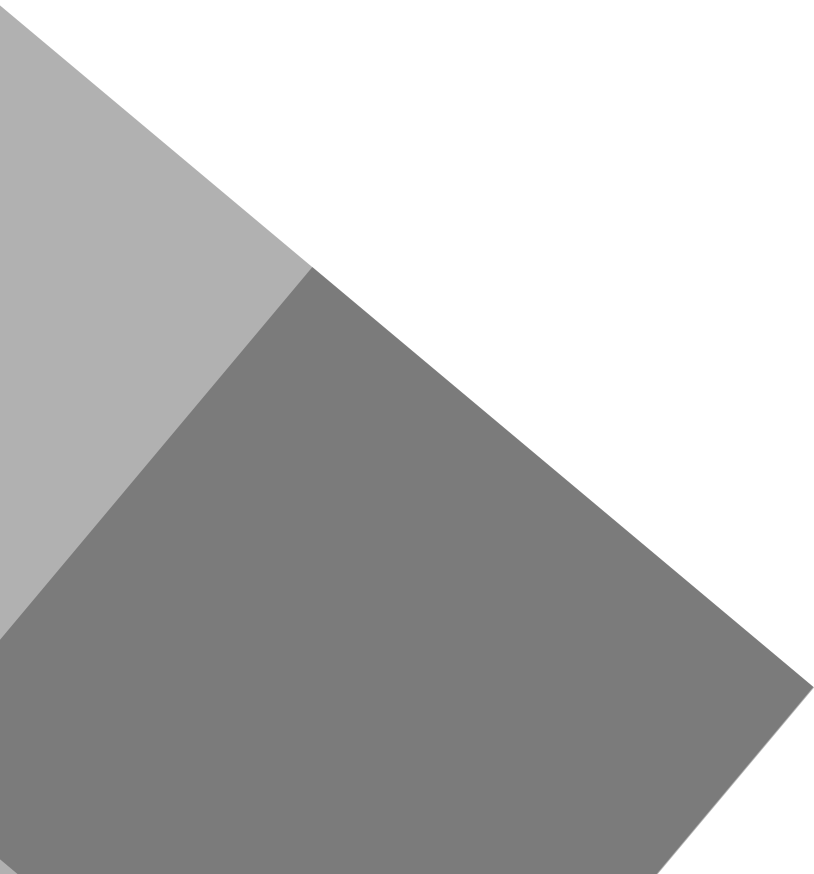























资源城市的“中年危机”
文/李隽辉
这是8座资源型城市的影像,在中国共有262座资源型城市。
它们中的一部分形成于建国之初,“矿市一体”模式占多数。 在262座资源型城市中,有67座属于衰退型。几年前,经济学专家肖金成曾去云南的“铜都”东川调研,回来后却不忍撰写调研报告,因为“如果要写,全是批评之语”。这些曾经为中国经济建设倾其所有的城市,在资源透支后,除了得到有限的“反哺”,现在更多的是长期承受来自市场经济规律下的生存压力。
八座城市中,辽宁阜新、黑龙江伊春、江西景德镇、甘肃玉门、陕西潼关和河北下花园是衰退型,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资源枯竭型,山西大同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分别是资源成熟型和成长型。
三个故事
阜新
2017年2月,苏铁强躺在医院17楼的病房里,看着辽宁台转播中央台的新闻联播,这是他在病房里不多的消遣之一。现在距离2014年的瓦斯矿难事故已经过去了两年多,苏铁强和死里逃生的工友们在医院也住了两年多。治疗烧伤的药早就停了,从膝盖往上的皮肤每一处都像是被人用指甲提了起来,像是包了浆的核桃皮,再也无法复原。“身上不得劲啊,总痒,到了夏天更难受,汗毛孔都烧没了,一身汗排不出去”。这次事故留给苏铁强的,除了烧化的耳朵和一身的“核桃皮”,还有无时无刻都在骚扰他的“刺挠”。
两年前,恒大煤业公司的五龙矿,苏铁强和工友们一起下井,下午一点半的时候,只听到“哐当”一声,他和工友们被从后面掀起的巨大气浪顶飞五六米远,晕倒在地上。等醒来的时候,矿洞里已经漆黑一片,苏铁强只觉得胸前发热,想把衣服脱下来,用手一划拉,只能摸到黏糊的液体,衣服基本已经烧没了。他坐在地上摸索着,找到了被震飞的矿帽,打开矿灯,找到另外的几名工友。几个人试着动了一下,决定互相搀扶着向井口移动。走了四五百米后,下井的救护队找到了他们。这次事故,和苏铁强一起下井的28名矿工没能活着升井。
还有的矿难事故,没有媒体报道,只是留存在经历者的脑海里。
张树良今年81岁,18岁从煤炭部技校毕业后,就一直在阜新市高德矿厂上班,1995年退休候,他又被当地一家私营矿场聘去做了电工,直到2016年去产能大潮中关门,他还没有离开。就在这家矿,2002年的时候发生了一起矿难。与张树良一起从高德矿厂退休又被另聘的常明发,在这次事故中去世。
张树良印象中的常明发是个大高个,白净净的“长挂脸”,有一膀子力气,人也朴实,干活舍得出劲。出事的时间是个春天,常明发刚刚从绞车工“升任”坑长,手下管理着一百多号人。下午两点钟,常明发所带的班眼看就要下班了,加上炸煤的火药也用完了,想早点收工的工友就对常明发说,要不早点下班吧。常明发看了看时间,还能放一炮,就去旁边的班借了8根雷管回来,打算再“整点”。常明发的班在墙上打了两个眼,为了让火力更大一些,8根30公分长的雷管分别都塞进了两个眼里。巨响过后,原本应该敲打明顶确认支撑的程序因为“赶时间”而直接跳过,没想这时煤层突然塌方,一个班8个人在开煤的时候被煤层压在了下面,后来只有两个人侥幸逃了出来,最终这次事故造成8人死亡,4人失踪。而这次事故,也并没有出现在官方的通报中。
早些年间,下井的矿工们普遍都喝酒,一是因为井下潮湿,另一个则是为了壮胆。“挣着阳间的钱,干着阴间的活儿”,这是阜新每一个矿工都会说的话。发生在这个地方的矿难事故实在太多,“死两三个人都不叫事儿”。现在,下井在一线采矿的工人们的待遇却缩水得厉害,有人在网上晒出工资单,每个月的工资还不到两千元。
潼关
桐峪镇是行政管理的名称,当地人更多的叫这里“零公里”。
零公里是个地标,以此为起点,向大山深处辐射的各个金矿矿洞则以距此处的距离来命名。
只要进了桐峪镇矿区的大门,就让人觉得是另一个世界了。刘月荣今年六十七岁,本地村民,是进山关卡的看门人之一。他说,几年前的时候才乱呢,零散的小矿和尾矿都已经包给了私人,矿主们经常会为了利益互相攻击,死人的事情常有。在采访中我几次和刘月荣相遇,一开始他总小心地试探我,问我是不是记者,我不告诉他。后来再遇到,他就神秘地笑笑,说,记者在山里的名声可不太好,之前有记者去发生矿难的矿上要钱,结果被打得很惨。
脸生的外来人会有这样的感觉:无论是下井的矿工、路边百货店的老板、往返矿上城里的小巴车司机,除了用眼睛,还会用话头好好“打量你”。他们说话办事务实简单,只能他问你,你回问的基本不搭理,顶多从牙缝里蹦出只字半语。他们不和你聊风花雪月、柴米油盐,也不认江湖,每个人都像是一匹独狼。
矿山上,矿工们分三班,开工的时候就顺着写有“点石成金”四个大字的矿洞钻下去,把矿石翻上来,碾碎了提取精华。村民们地也不种,跟在后面捡拾尾矿。山里所有的一切好像都围绕着金子。有人收集村民捡拾的尾矿,在手工作坊里用汞提取出金子,转卖给零公里的商铺,市面上290元每克的金子这里只要275元。
和收金铺一样多的是小姐们的门头房。太阳出来的时候,她们就穿戴整齐,有的倚在门框上,一边晒太阳一边招呼着路人“进来耍”。刚来镇上的时候,她们和山里的金矿一样年轻有活力,现在大都已经过了四十岁。闲散的时候她们会聚集在一起,隔着马路能听到聊天时传来的笑声。她们大多单身一人,身边没见有孩子,有的却会养只小猫,陪着自己。
玉门
玉门的建立始于建国前的石油开采,比大庆早了近20年。一座石油基地背依祁连山脉,就建在茫茫的戈壁滩中,随后围绕着这个基地,各种基建和服务行业出现,慢慢有了城市的模样。随着石油的枯竭,市政府和油田基地搬离,9万多居民外迁至嘉峪关、酒泉和玉门镇,也就是现在的玉门市。
王建兵是玉门人,今年50岁。他从小眼睛就坏了,一点光感都没有,为生存学了按摩,在紧挨着玉门公园门前的三角地开了一家按摩店。他回忆,年轻的时候,马路边发行彩票,一上午就都卖完了。中午赶过去,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刮完的彩票。“你想想人多少,现在人都没有了,现在一到双休日,都静悄悄的”。人少了,王建兵的按摩店店里原来有十个床位,雇了7个按摩师,店里面一天到晚都是人,现在只剩他一个人了,一天只能按三四个。
随着人们搬出,城市的经济系统重新构建,什么值钱,什么不值钱在随后的日子里反复被纠正、评估。市中心的房子,2006年的时候一套楼房才三千块钱,现在稍微涨了一点,值两三万。王建兵按摩一个人,从早先的15元也涨到了30元,但也只能解决温饱。
(此拍摄项目由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资助)

欢迎联系我们
如果您有悄悄话想告诉我们,欢迎私信@看见微博;
如果您也有故事想通过摄影的方式来讲述,欢迎来稿。
邮箱:sinaphoto@vip.sina.com
《看见·看不见》新书已上市,讲述有力的图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