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等现代科技已经普及的中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依然居住着原始牧民克里雅人。四百年来他们隐居在这片大漠深处,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是“大漠隐者”。然而随着公路的修建和旅游的发展,克里雅人还是与现代文明遭遇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在融合与冲突中悄然发生着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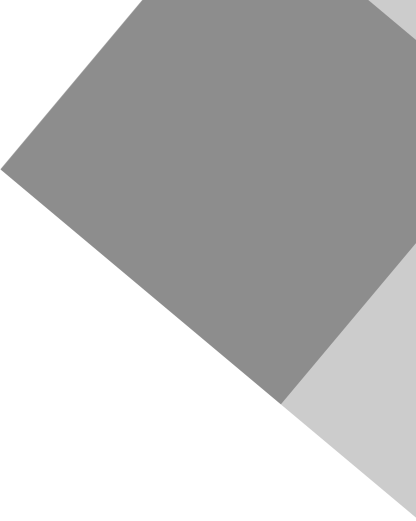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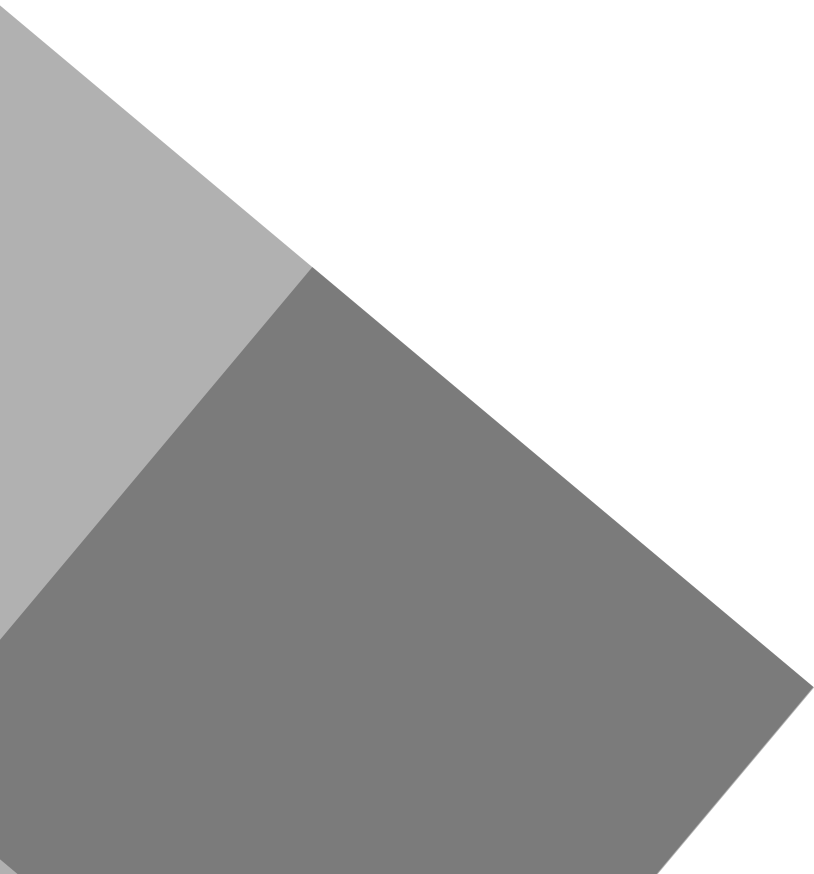


















最后的“大漠隐者”
文/张新民
达里雅博依与于田县有240公里的里程,要沿着克里雅河边的沙漠和芦苇荡穿行。这是最考验技术和胆量的冒险。好在有热杰普、艾力、图达洪三兄弟和一些年轻人,凭借着无畏和勇敢,驾驶着环塔拉力赛淘汰的旧车,和各种老掉牙的进口越野车顽强地前行,用12个小时的时间终于走完这段艰辛的道路。
骑了17天毛驴
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里,克里雅河即将消失的地方,被称作达里雅博依。这里的居民沿河游牧,离群索居,而且恋土难移,被人们称作沙漠里的“原始部落”。
达里雅博依人的来历,一种说法是西藏阿里古格王朝的后裔,为逃避战乱翻越昆仑山进入了这片绿洲;另一种说法是他们就是这里的沙漠土著民族;第三种说法则是达里雅博依人是2000年前神秘消失的古楼兰人的一支。
1896年1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沿塔里木盆地的克里雅河追寻到沙漠的尽头。他想知道,那最后的几滴水挣扎到哪里为止。但他突然发现,这里不仅有成群的野骆驼在奔跑,而且也是大批野猪的乐园,更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竟有一个牧民群落在这里生息着。
过去了半个世纪后,1959年,人民政府派人找到这群隔绝的维吾尔人,并为他们建立了达里雅博依村。不幸的是,“文革”中,他们再次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1981年,于田县畜牧局局长巴克图地和县城的一名医生、一个教员、一个公社代销员,以及负责生活的干部第一次去达里雅博依。在整整骑了17天毛驴后,他们终于到达了达里雅博依村。当地村落里所有的人都来看望他们。“这村子连一个馍馍都没有。”最后他们把自己带来的干粮、核桃葡萄都给了村民们,然后又骑着骆驼,没日没夜地走了16天回去。
回到于田,巴克图地连家都没回,赶紧向领导汇报大河沿的情况,书记带领大家开始修路。81个20-40岁以上的年轻人,经过了87天的大战,终于在沙漠里修筑了一条勉强能行车的简易土路。刚开始没有司机敢去,巴克图地先让自己12岁的大儿子热杰普跟车为车子一路加水。最终2个拖拉机、21个骆驼、31个毛驴,经过7天的艰难跋涉,给达里雅博依的村民送过去了面粉和衣服。
铺了一半的柏油路
以前的达里雅博依,村里没有房子,羊走到哪里,人就去哪里睡觉,大风来的时候,“茶也喝不了,水也吃不了”。而且每年克里雅河都会洪水泛滥,还经常改道,克里雅人居住的地段属于400年前的古河道,有时候洪水来了还要搬家。不过,每家人最主要的财产是100只左右的山羊或者绵羊,换个地方就是了。
后来,家家住上了柳条编制后用泥巴加固的草房,木骨泥墙的大客厅,细细的泥土铺成的地面。细土是润润的,并不干燥,房子显得简陋而整洁.
以前,当地的食物主要就是一种叫“阔麦琪”的烤馕:把死面埋在沙子和灰烬里闷熟的面饼。有了路后,司机们经常会从于田带蔬菜和东西来。村民亚生江家有人开车跑这条线路,他们家吃的就相对来说丰富点,基本上不再吃“阔麦琪”。
不过修路带来了新鲜蔬菜,也带来了担忧。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有一个叫做牙通古斯的原始村落,和达里雅博依类似。1999年11月,牙通古斯村终于修通了一条柏油路,从此村子由神秘变得透明开放。当地的安迪尔甜瓜产业为农牧民带来了很高的收入,可是后来随着旅游的开发,人们越来越失去了对这里的向往,牙通古斯就在媒体和人们的记忆中逐渐被淡忘了。
人们担心牙通古斯村的今天,就是达里雅博依的明天。
2017年,达里雅博依到于田县240公里的道路,已经有一半铺上了柏油。不过鉴于牙通古斯村在前,当地干部认为公路理想的状态就是修一半留一半,这样旅游开发的收益会持久点。
不过2017年,达里雅博依村被列入拟创建的4A级景区名录。今年,这里的人们和学校、卫生院等也开始陆续迁往距于田县92公里的新区,而克里雅河的流量正逐年减少,未来甚至可能会干涸。达里雅博依那种安静,那种自然惊艳的美,又能存在多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