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哈尔滨北上,就是作家萧红笔下的呼兰河。4月,呼兰河刚开始解冻。然而在哈尔滨以北300多公里的伊春,冰雪仍未消融。这座大片林场催生的城市,2008年被国务院列入首批12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经济下滑,人口流失严重。所幸,森林资源是可再生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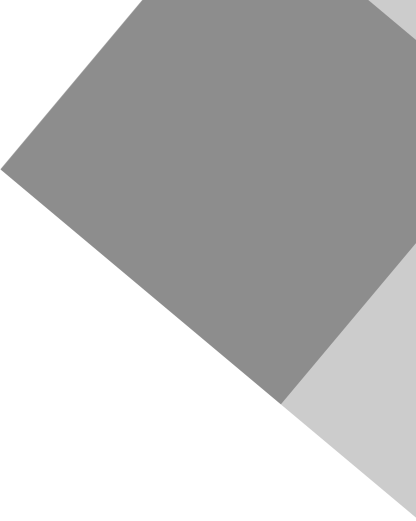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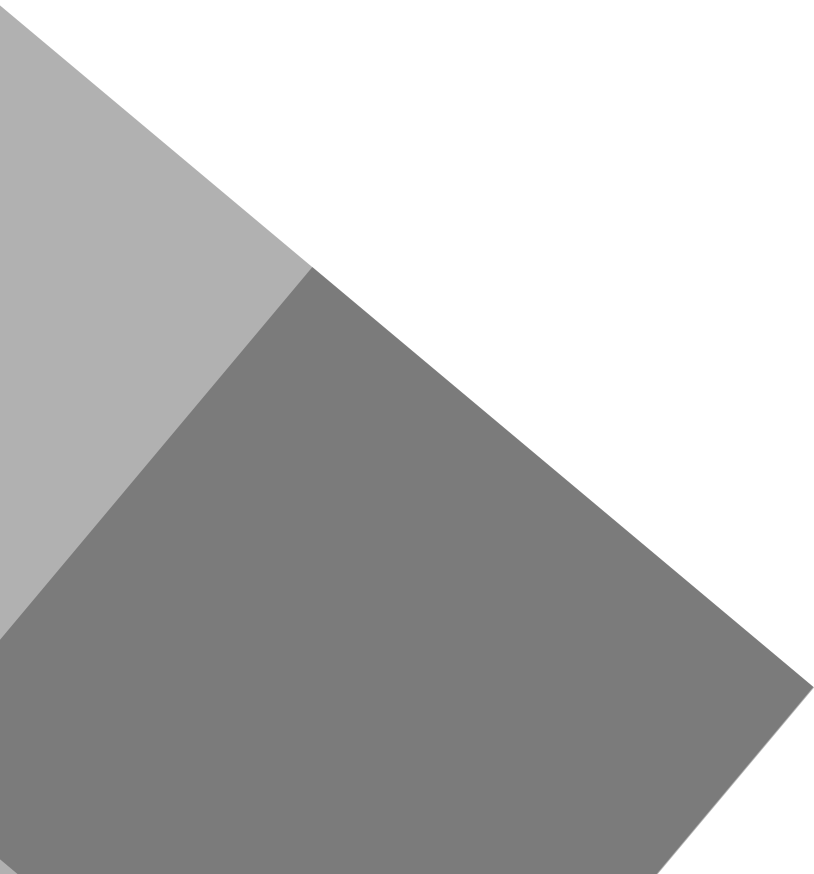


















寂静的春天
图|文 Stamlee
4月,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
出哈尔滨,北上,就是作家萧红笔下的呼兰河。此季,呼兰河已经开始解冻,刚刚消融,还带着雪的大块浮冰,随着河水冲向下游。
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还要再往北300多公里的兴安岭腹地——伊春。
所采伐的原木连接起来可以从地球到月球绕六圈半
伊春,位于中国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面积3.64万平方千米,与俄罗斯隔江相望,伊春市界江长246公里。伊春市的森林覆被率为82.2%,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
这里,有着被命名为“林都”的机场。伊春,曾是树木参天,绵绵延续,横亘千里,不知所极的原始森林; 这里背靠小兴安岭,天蓝、地沃、水纯。
兴安岭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广袤的森林资源,使它具有无可替代的生态功能。它是东北松嫩平原、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乃至东北亚的天然屏障,又是黑龙江、嫩江的源头。大兴安岭的森林和湿地共同维系着两大流域的水平衡,发挥着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护水土、防风固沙等作用,承担着建设“国家生态安全重要保障区”的重任。
1948年,伊春林区的森林蓄积高达4.28亿立方米,可采成熟林蓄积达3.2亿立方米,在国家以“木材生产”为主的林业发展方针主导下,60年来,伊春共为国家提供优质木材2.4亿立方米,所采伐的原木连接起来可以从地球到月球绕六圈半。
因木而聚,也因木而散
短短半个多世纪,昔日“林老大”的光环就开始日渐暗淡。同东北无数个曾经繁荣的城市一样,计划经济无休止的资源开采,导致林业资源枯竭,当地经济危困,民生艰难。
2008年,伊春被国务院列入首批12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国家终于暂停了向兴安岭“要木材”。而后成为“全国唯一的国有林权改革制度试点和林业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城市”。
又是近10年过去了。
所幸,林业资源与其他矿产资源的枯竭,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伊春与鸡西、鹤岗、大庆等煤矿或者石油开采相比,木材是可再生资源,停伐、封山就能看到希望。
伊春是一座大片林场催生的城市。
当年,诗人郭小川在《祝酒歌》里这样描写伐木场上的盛况:一声号令下,万树来归队,冰雪滑道上,木材如流水,贮木场上,枕木似山堆……
车辆行驶在兴安岭狭小的雪道上,依稀可以想象,路两旁,当年成群伐木工人忙碌的身影,隐约可以听到那隆隆作响的伐木声。
无论伐木、装载、运输,林场的工作都是成群结队的,也必须成群结队。就像兴安岭山区里的大多数餐馆一样,座位的设置也是4人面对面的排座,又或者是8人以上的大圆桌。如果是一人就餐,那是件非常尴尬的事。这里的菜量之大,也许就是人们要结伴的需求。
因木而聚,也因木而散。从减少木材砍伐,再到彻底禁伐,就是最近这5年来的事。与之相伴的是人口迅速流失。人,是一座城市发展的基础,但对伊春来说,人口少,也成了一种“资源”。
清晨,几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来到伊春河边,身后是包裹严实的小贩,他们推着倒骑驴的小三轮,踏冰而过。这里的春天似乎还未来到。
这个位于黑龙江省北部的神经末梢地区,它的春天来得迟缓并且短暂。又或许是,少有人打扰,这里的春天也更显寂静。
“停伐”是个沉重的词汇
从哈尔滨到伊春300多公里已经全程通高速,但因为国道、省道相间的小路上,少有车辆,4个多小时也可以到达。出呼兰河,就开始进入兴安岭林区;一路上,见到最多的就是林业防火检查站,每隔5公里左右就有一个。
“停伐”,曾经在黑龙江森工系统72万干部职工心中是个沉重的词汇。它意味着告别长久以来依靠砍树伐木的生存方式。
王林河是小东沟检查站的护林员。他的值班小屋的门前写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放下斧头锯,奔向黑土地”王林河曾经是林区伐木工人。在伊春全面停止了商业性采伐后,成为村一级的护林员。护林员,有自然村级护林员,行政村级护林员,林场护林员和国际专业护林员。像王林河这样的,每到春、秋重点防火季节时,才会轮到去值班。每月有几百元的补贴。
其余时间里,他和村里其他留守的老人一起以种黑木耳为主要收入。
莽莽林海,红松擎天。王林河指着不远处的那片林子,这里100棵树中,超过30棵都是红松,不仅量大,而且树木构成中红松种类多,因此叫红松的故乡。
“以前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越砍越穷、越穷越砍。80年代末期,那三、四人都抱拢的大树,都是开着拖车从山推下来的,堆得比对面的那防火塔还高,可你看看,这日子还过成这个样子。”
王林河有个女儿,1990年出生在林场,去年嫁到厦门去了。自从停伐后,林场里就留不住年轻人,远的,去了广东、海南工作;近的,也在哈尔滨一带谋生。现在林场里,最年轻的也就是46岁的王林河自己了。
“不过,去年,女儿带着外孙子回来过一趟,她看着家里的木耳培育房后,说是要开家网店,帮我们销售……”王林河钻出暖棚后,点了支烟,十分认真地“谋划”起,如何把对面那间老房扩建成另一间育苗间。停伐后的林场,剩下最多的就是空置的老房子,一间间用木头搭起来小板房,外面包裹上一层塑料膜,就是一间暖房。
小东沟的路边竖着一块林场里最大的一块广告牌“刘三庄鹿场”。那是王林河最羡慕的刘村长家。
这是一个梅花鹿养殖基地。刘村长正扛着一袋苞米粒,边散边吆喝:“吃啦!吃啦”。生性胆小的梅花鹿,竖着耳朵,四处张望一圈,然后从小木屋里轻巧跃出。“这窝小鹿是我从山里挖药材,捡来的,都7年,现在都 长成这么一大群啦!你看你看……”刘村长乐滋滋说。
榛果、蓝莓酒、红松籽、松籽油、木雕、药材……村长还开着一家小饭馆,饭馆的大厅里就展示着当地生产的各种生态产品。
地窨子、马架子、撮罗子……饭馆的墙上画着那些过去鄂伦春狩猎户居民居住的地方。
“现在已经找不到这些物件,他们早就下山定居了。”刘村长看我盯着那幅画,就来解说。
“也不一定,去一些深山里,还能看到搬空的桦皮小圆棚,你下雪前,还看到过。”王林河补充道。
高峰林场的周海浪,18岁离开林场,外出经商。
2015年,他又回来了,得知家乡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他投资了当地一个风景区。虽然盈利远未达到预期,但周海浪看好它的前景。
“没有人打扰的林子,多好啊”
空气中飘着特有的松香味,那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山间小木屋里,清晨,被林间的鸟叫声唤醒。
王林河兴奋地叫我们一道进山去追狐狸。
昨晚,林间又下雪了,他在取水的小河边,发现一窜十分清晰地狐狸脚印。
我说“别去了!你也别去了!没有人打扰的林子,多好啊,让它多一会儿寂静吧。”
王林河愣了一下,然后突然大笑起来“对!对!”。
但愿,王林河是真的明白了。
从呼兰河到伊春河大约300多公里,我希望呼兰河的暖流可以来得慢些,再慢些,这样伊春河可以一直冰封,直到度过这个没人打扰的寂静春天。

欢迎联系我们
如果您有悄悄话想告诉我们,欢迎私信@看见微博;
如果您也有故事想通过摄影的方式来讲述,欢迎来稿。
邮箱:sinaphoto@vip.sina.com
《看见·看不见》新书已上市,讲述有力的图片故事。











































